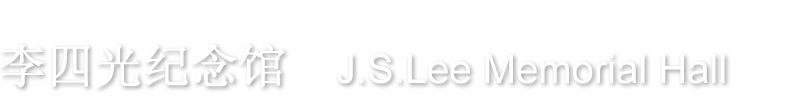

1955年,李四光(中)与本书编审帕夫林诺夫教授(左一)在北京。
不久前,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地质学家在来京访问时,将一本父亲珍藏近60年的俄文版李四光专著《中国西北部旋卷构造》赠送给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所和李四光纪念馆。2017年12月26日,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看到相关报道后,特地从书柜中找出了一本同样的书。原来,他便是此书的翻译者之一。
已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面对这本保存完好的灰蓝色精装著作,他仿佛又听见了上世纪50年代莫斯科街头繁茂树丛中的啾啾清啼,又置身于那韵味数十年不变的优雅都市。翻开熟悉的扉页,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记忆倾泻而出。
故事发生在1955年。那是赵鹏大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第二年,一天,他的指导老师雅克仁教授忽然找到他,说苏联地矿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希望见见他。部长召见一位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会为了什么?
见面后赵鹏大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当时中国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赠给他一本自己最新出版的专业著作《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安德罗波夫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尽快把这本书翻译成俄文。
他对赵鹏大说,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很有道理,我想让苏联地质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地质学家独创的地质力学。他还说:“你们中国发展得很快,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就会从各方面超过我们苏联的。”部长很和蔼,也很直率,给赵鹏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赵鹏大的俄文非常好,日常学习生活都游刃有余,但毕竟这是一部创新性的地质专业著作,里面有很多全新的词语,这就给翻译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而赵鹏大作为研究生在苏联的学习是有期限的,一般情况不能延期,如果耽误了学习可怎么办?况且工作量很大,一个人也应付不来啊。随即,赵鹏大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报告了此事。
大使馆回复说,一定要把这个任务接下来、完成好,国家会给你最大的支持,实在完不成就把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延长一段。最终,赵鹏大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并邀请与他同时出国在该校学习大地构造的研究生钱祥麟来共同承担这个任务。
莫斯科的冬天银装素裹,特别是圣诞、新年的前后,展现着一种圣洁的繁华。不过,浪漫活跃的赵鹏大在跨越1955年和1956年的这个冬天里,完全没有感受到身畔的热闹——他和钱祥麟整整三个月几乎哪里都没去,一头扎进了旋卷构造的世界里。
翻译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是一个创造性解释的过程。翻译李四光的著作,最费时间、费心力是一些独创性词语和理论的翻译解释,他们发现仅“地质力学”一词就有多种不同的译法,为了统一,更为了确切,他们查阅了大量书籍文献,仔细研读李四光的其他著作,体会理解地质力学等理论的实质和内涵,再经过认真的比较和斟酌,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交由该校的构造地质学家、曾于1953-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帕夫林诺夫教授编审把关。
后面关于出版的过程,赵鹏大不甚知晓。1957年末,他按时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任务,以优异的成绩和精彩的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并在全苏储量委员会实习了一段时间后于1958年3月回国。现在他手中的这本书,是后来由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阿里斯托夫教授辗转送达的。
翻译是文献积累最有效的方式,也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会和碰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地质科学交流火热,而这部著作的出版,也的确更好地扩大、加深了当时中苏两国地质界的相互认知。
安德罗波夫曾表示,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力学不仅仅是大地构造的一个学派,而且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代表一个时代的地质理论。他在俄文版《中国西北部旋卷构造》的序言中称李四光是该领域研究的“拓荒者”,并写道,“在旋卷构造一书中,李四光院士特别强调了主要表现在上层的地壳水平运动”,其“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各种矿产的位置,因此不仅具有科学意义,更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他还提到,李四光的理论还需不断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地质勘探工作会更快、多边验证或实践这一理论”。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这部译著正式出版的1958年,苏联科学院选举李四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授予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对于赵鹏大而言,这一阶段对地质力学、旋卷构造的研究理解,也为他的学习、成长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力学与地质紧密结合,带来的是研究方法的改变,而地质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科学,本就应该与更多的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或许,这也为他之后在数学地质、数字地质领域取得的成就,增添了一份动力。
一本书,穿越60年时空,不仅联结了两种文明、两种文化,更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地质学家对科学精神共通的释放与追求。(转载自国土资源报)